包拯是宋朝人,但宋代的戏曲却没有“包公戏”。元朝兴起的“包公戏”,终于在晚清大观了。几百年来,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、南剧、话本、评书、小说、清京剧等地方剧;近代以来,包公案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。无数中国人通过“包公戏”了解古代司法制度和司法文化;一些学者还以“包公戏”为样本,认真分析了传统的“人治司法模式”,反思了“中国传统司法不能近代化的重要原因”。然而,“包公戏”的故事作为一种民间艺术,是在宋代文明湮灭后才兴起的,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的。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代司法场景与宋代的司法制度完全不符。假如认为“包公戏”展现的是宋代的司法过程,那就要闹出“错把冯京当马凉”的笑话。现在有必要澄清宋朝被“包公戏”掩盖的司法传统。

【尚方宝剑三刀丹书铁券】
就像《封神榜》中的神仙出现一样,法宝必须展现出来。“包公案”的包青天也携带各种道具,代表皇帝的皇赐和最高权力。元杂剧中只有“势剑金牌”,明清传说中出现了权力道具“大批发”。:“(宋皇)给我一把金剑,两个铜断头,一个锈木,一个金狮子印,一十二皇棍...给我一根黄木枷锁和一根黄木杖,切断皇室亲戚和大臣;黑木枷锁和黑木杖,专断人间事不平;槐木枷锁槐木杖,要打三司九卿;桃木枷锁桃木杖,日夜断阴。”
这里的“势剑”和“金剑”,即所谓的尚方剑;“金牌”是丹书铁券,俗称“免死金牌”;后来,“铜台”发展成为我们非常熟悉的“龙头台”、“虎头台”和“狗头台”。龙头台杀贵族,虎头台杀官员,狗头台杀平民。包青天凭借这些神奇的法宝,成为历史上最厉害的法官,遇佛杀佛,遇鬼杀鬼。有趣的是,包公要对付的罪犯有时也有类似的法宝,比如根据元杂剧《包待制智斩鲁斋郎》改编的潮剧《包公智斩鲁斋郎》、川剧《破铁卷》都讲述了世家公子鲁斋郎依靠祖传的丹书铁券护身的故事,无恶不作,无法无天。所以好戏来了:杀伤力最高的尚方宝剑能打破防护力最高的丹书铁券吗?从戏文上看,似乎破不了。最后,包公不得不采取非常隐瞒的手段,在刑事报告文件中将“鲁斋郎”写成“鱼”,欺骗皇帝批准死刑,批准文件,然后改为“鲁斋郎”,将大恶霸押入刑场。

因此,本应以法律为标准,区分黑白是非的司法判断已经演变成谁拥有更强大的权力道具,谁就赢得权力对抗。正如周星驰电影《九品芝麻官》所示:一方牺牲皇家黄夹克来保护自己,另一方牺牲可以打破黄夹克的尚方剑,另一方则打破尚方剑是假冒产品。这也证实了批评传统人士对“人治司法模式”的指控。然而,在宋朝的司法过程中,如此戏剧性的权力道具决斗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包公不可能持有尚方剑——宋朝没有给大臣御剑和专杀权的制度。直到明朝万历年间,尚方剑才出现,皇帝才赋予持剑人“如我亲临”和“先斩后奏”的超级权力。包公的三口断头台是民间文人幻想的刑具。历代都没有把断头台列为行刑工具。很可能是进入元朝后,民间文人从蒙古人用的断头台上得到了灵感,想到了给包公打造一副铜断头台的情节。
至于所谓的“免死金牌”,虽然北宋初和南宋初在战时,宋朝皇帝给了李重进、苗傅、刘正彦等将军丹书铁券,以安抚当地军阀。然而,丹书铁券并不是宋朝的常规制度。此外,随着李重进、苗傅和刘正彦的叛变,他们失败了,自焚并受到惩罚。铁券被销毁,铁券制度不复存在,南宋人程大昌说:“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制度,也缺乏古代的东西。因此,在宋朝的司法过程中,丹书铁券不可能对抗尚方宝剑。丹书铁券直到明朝才成为常制。事实上,宋人的法律观念排斥免死金牌。他们说:“法者,天子与天下共同……所以王者不分亲疏,不分贵贱,与法律一致。宋太宗时,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熙犯了一个错误,并在皇家历史上被丞弹劾。元熙心中不平,诉于太宗:“臣天子儿,以犯中丞故,愿给予宽恕。太宗说:“这个朝廷仪制,谁敢违之!如果我有,臣下还会纠结;汝是开封府尹,不奉法邪?”@ 贵为王子的赵元熙“论罚如式”。

宋太宗也想保护犯法的亲信——陈州团练让陈利用自己被太宗宠坏,杀人,被朝臣弹劾,本该处死刑,但太宗故意保护他,说:“万乘之主不能保护一个人吗?宰相赵普抗议道:“这巨甲犯了十几个死罪。陛下不杀,则乱天下法。不幸的是,这一竖子,何足惜哉。最后,太宗不得不同意陈利用死刑。皇帝本人无法保护犯罪的亲信,更不用说免死金牌了?由此可见,宋人的司法并不依赖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,而是强调三尺之法。韩晋卿,生活年龄略晚于包拯的大理寺卿,曾被皇帝任命,前往宁州治狱。按照惯例,韩晋卿上任前,应入对(即入宫面圣),请皇帝做工作指示。但韩晋卿拒绝入对,说:我奉命办案,以法律为标准,国法摆在那里,不必征求皇帝的意见,以免干扰司法。因此,至少在理论上,宋朝法官只需要依靠头上三尺的法律,就不必看手中是否有尚方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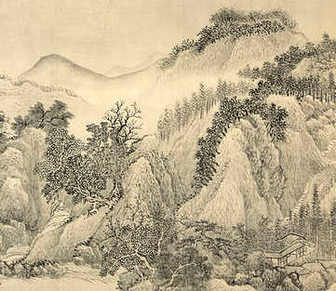 包青天包拯没有狗头:包公戏扭曲宋朝司法
包青天包拯没有狗头:包公戏扭曲宋朝司法